《口腔文史》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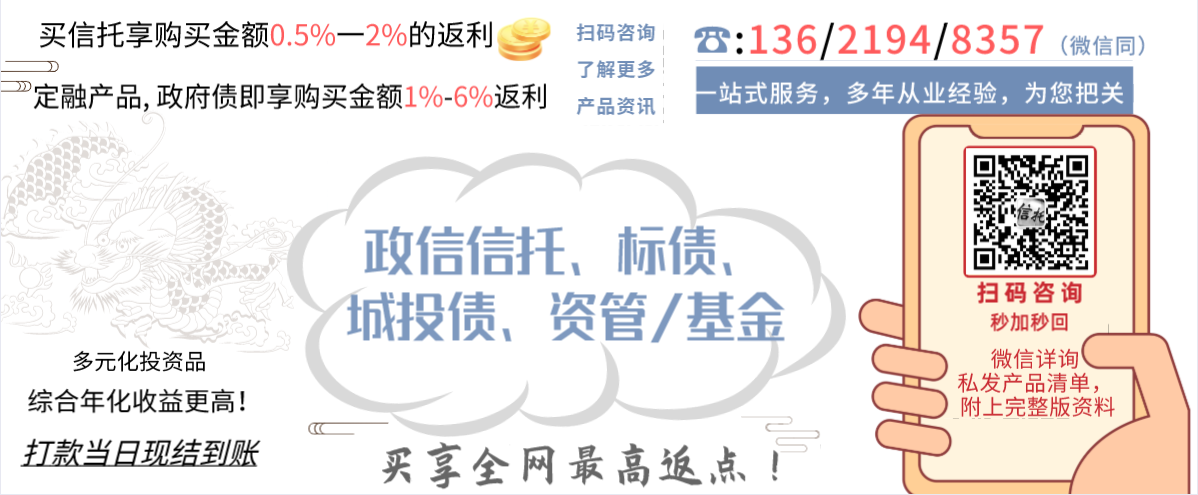
主办: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口腔文化专业委员会
文/陈泽先
前言
1936年的成都华西坝,诞生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两个牙医学女博士:黄端方和张琼仙①。
根据位于大邑县新场古镇的《华西百年校史展》载,1910 年华西协合大学建校之初,华大学生尤其是女生,都来自省内富家的优秀子弟。二十年代初,首次进入华西的 8 位女生就是成都及四川有名的大家闺秀。另外还有一类考生,则是出自各地教会发现推荐选送的优秀贫寒子弟,比如中国的第一个牙医学博士黄天启,就是谢道坚传教士1916年从乐山保送入学的。黄端方则由基督教美以美会资中分会 1928 年选送。
说来惭愧,尽管我一直同母亲在一起生活,但对她的印象却很模糊,她的经历知道更少。感觉就是一个慈祥的母亲,一个医生,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口腔科主任而已。四十年来,只有一次在给我女儿的信中,有过一些零碎模糊记忆整理。两年前,我认识了一位华西校友会的同龄人,建议书写我的母亲。在她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开启了对母亲黄端方生平的寻踪之路。
真没想到,从四川大学档案馆学生学籍部,竟查到了90年前华西协合大学学生黄端方完整的学籍档案──母亲于1928年9月 5日,亲手填写的这份《学生入学履历表》,一个个秀丽端庄的字迹,让我又看到了别离了 42 年的母亲。
1928年9月5日黄端方亲手填写的《学生入学履历表》
从这份表格,可以发现三条重要线索:第一、她在上大学之前,已经教过五年书, 有了中小学的教学经验;其次,她对于在学校实行“委员制”民主管理,有“不能忘之”深刻印记;最后,当问及毕业后的打算,她填写了“行医兼作个人佈道者”。从她后来的一生经历看,可以说都同这三点有关──这是后话了。
2020年9月,在我姐姐陈恕庸那里,发现了母亲写于 1965 年的两封亲笔信,信中对她的上半生有清晰的回忆和记载,澄清了我以前的很多模糊认识。
黄端方给女儿的信
根据这些线索,当年十一月,我到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随后又在四川大学档案馆查阅了与黄端方相关的多个案卷,还拜访了好几位与母亲及华西大学有关的人员,获得大量材料。通过这段时间的资料整理,让我充分感受到:母亲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女性。
黄端方肖像/华西口79吴友农绘
以下,就是依据这些材料,对母亲黄端方的回忆和描述。
第一部分 出身贫寒的美以美会教友,靠勤奋走进华大
四川省资中县,南距内江 40 公里,北到简阳 90 余公里,是成都到重庆的交通要冲之地;也是 1991 年经省政府批准,成渝线上唯一的历史文化名城。沱江自北而南,穿老城而过。江东岸树木苍翠的重龙山下,资中城人杰地灵,历史文物很多。这里出了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状元街上有闻名的文庙,其中孔子的站立像在全国不多。与之呼应,文庙对面还有全国少见的武庙,不但供奉着关羽三代的神位,还有岳飞在一旁陪祀。
在状元街南头的小北街,就是母亲黄端方 1903 年的出身地。家里为她取名“端方”──是“方”而不是女孩子常用的“芳”,取希望她“端方正直”之意②。
我外祖父黄荣楼是个中医,为监狱的犯人看病。黄荣楼性格孤僻耿直,微薄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母亲为人家缝补衣裳,有空时也随父亲学点针灸。黄端方排行老四,之上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父母的这点收入不够全家开支。每到年关,常会有债主上门催债。为了减轻一点负担,母亲七岁那年,跟她的母亲(我外婆)到荣昌县投靠在县衙门当厨子的二舅父。他们全家四口,加上我母亲、外婆二人,六口人同住官立女校的一间矮小杂屋里,进出门都得俯首弯腰。女校每天会有剩菜剩饭挑出来卖,一大瓢才两文钱,够六个人吃了。就这样在荣昌过了一年多,好像就从没有吃过新鲜菜。我外婆用跟随丈夫学到的一点中医技能,替穷人用麻线灯火做针灸,找补点开支。
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外婆和舅父都执着地认为,女孩子必须要读书,才会有好日子过。于是让母亲在县福音堂入了基督教。从此,生活向她展开了新天地,有了上学的机会。后来回到资中家里,依然是教会的关系,继续在资中美以美教会小学读到初小毕业。这时候,母亲的天赋开始被老师发现。于是,美国传教士曾启贤把她带到成都华美女校念高小。两年毕业后,转到布后街教会的女子师范继续就读一年。
尽管这几年在教会学校上学免费,但欠下的钱还是要还的。读书期间,黄端方先是被派到隆昌县福音堂女校教书一年半;继而又被派到荣昌烧酒坊去开办福音堂女校任教兼做教务。三年时间,母亲工作的业绩很好。之前念书的学食费还清了,获准回到成都在华美女中继续上学。她学习勤奋努力,三年时间上完了四年制的课程,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第一名。
1926 年母亲中学毕业,再派回资中敬德女中任教。此时适逢蓬勃于沿海诸省的“非基督教运动”也开始深入四川,学校的传教士都撤离大陆到马尼拉避祸。接下来一年多时间,母亲参加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卓有成效。传教士们 1927 年返校后对母亲这段时间的工作十分赏识。
次年,美以美会保送母亲进入华西协合大学,上牙科。这时,她已经 25 岁,比同学都大好几岁,大家都叫她“黄姐”。
从贫民到进小学、上中学,念师范直到进入华西协合大学,十多年间,反复地读书、教书,管理……,都源于教会的资助和自己的拼搏奋斗。她立志成功、要改变命运;也决心一生回报教会。
第二部分 八年勤工俭学,攀登中国牙医顶峰
黄端方 1928 年进入华西协合大学,先读了三年预科(第一年普通预科,接着两年是牙科专业预科)。从写于 1932年6月的那份“对学分说明的便签”来看,她因为学习成绩优秀而免修了部分学分。本来应该念八年的牙科,从一年级(1931 年)跳过了二、三年级,直接上四年级(1932年)。
在课表档案中发现的一份1932 年的手写函件--对学分说明的便签。记录了关于黄端方所修学分的情况。
释文:黄端方,生物学系。根据 1928 年之章程计算,预科应修 42 学分,正科应修 76 学分,两项和(合)计共应修 42+76 = 118 学分。伊现已修及免项共 13+21+26+24.5 = 84.5学分应选,尚欠 118-84.5 = 33.5 学分。故在第三、四两年平均每年修17学分。
(19)32 年 6 月 27 日
(xxxx 英文签名)
在四川大学档案馆存有的华西协合大学的学生资料。作者查到黄端方 1928-1934 年课表,此处仅列出黄端方 1932 年的课表照片供读者浏览。
在四川大学档案馆存有的华西协合大学的学生资料。作者查到黄端方 1928-1936 年的成绩单,此处只列出黄端方 1935 年的成绩单照片供读者浏览。
当年的华西钟楼与荷花池
华大怀德堂,入学报到和举行毕业典礼的地方,后为学校行政办公楼
在求学期间,深知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她学习更加刻苦。因为幼年出麻疹,与常人不同,她的水痘出在耳鼓膜上,虽然身上没落下疤痕,但听力却大大受损。所以学习相同的功课,她得投入比别人更多的功夫。母亲讲过,在学人体解剖课时,她很长一段时间,在枕边都放着个骷髅头,摸着数着入睡。
在 1928-1936 年的八年学习中,母亲每年都是考试的奖金获得者,免缴学费。其他的伙食费零用钱,则主要靠寒暑假打工的报酬来支付。平日里一旦有空,她会手织花边,在饲养场(大家称为“丁洋人”的 Frank.Dickinson 所办)喂养鸡鸭。母亲利用自己当年的教学经验,周末作家庭教师。到了高年级,为了学习更多的临床知识,她还在课余到四圣祠街的仁济医院内外科实习,返回时,顺路也到天仙桥的肖氏产科学校教解剖学。一天下来,已经疲乏至极。当年收到了解剖学教学的费用30元。
我在地图上查过,从华西坝女生院经南台寺东去,过安顺桥,沿城墙向北,经过府河边的天仙桥南、北街,到水东门后,西拐到望福街再经天涯石最后到四圣祠, 来回路程差不多超过 5 公里,母亲回忆说如此每天回到寝室都疲乏至极。
总之,那时黄端方是学校里出了名的踏踏实实的贫苦勤工俭学学生,哪个部门有了工作都喜欢来找她,比如替教授磨牙制片、喂养实验动物等等都做过。”
位于华西坝东头的女大院
牙科楼正面, 现为华西临床医学院;楼前为医院停车场
1936 年,母亲以牙科 1936 年班第一名获得博士学位,并准予获得加拿大牙科的毕业生标准──“裴塔裴”荣誉。她的毕业论文为:《A study of Dental Caries and Dietary Conditions among Students in Chengdu》(摘自《华西口腔百年史话》 王翰章编)。不知道这个选题是不是由她自己选定,但确实反映了母亲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深切人文情怀。
1936 年华大牙科毕业照:1936 年 6 月华西协合大学牙科、本科毕业生和院校教师们的合影。前排左三至左八为当年牙科的六名毕业生:左三张书林③、左四为张琼仙、左五为黄端方、左六夏尔琪(A.Sharevitch,俄国人)、左七夏耀珊、左八张乐天(其中夏尔琪和张乐天均由北京协和派来念博士的);其他教师有左一邹海帆、左二刘延龄,右一莫尔斯、右二高文明、右三吉士道 (当时林则回加拿大休假未在校中)。(此照片为华大杨振华教授保存,由成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何溢老师提供)
母亲数年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态度,以及优秀的学习成绩,深得牙学院院长、恩师林则的喜爱和关注,时任院长吉士道(林则在加拿大休假)准备让她留校并送到加拿大深造。
第三部分 二进华大,潜心发展中国牙医教育事业
出乎教授们意外,母亲并没有在华大留下来。
原来,就在毕业之前,她已经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牙医专科学校。中央大学是中国政府独立办的最高学府,对从小仰仗教会、跟着外国人求学长成起来的黄端方很有吸引力——既感恩又渴望摆脱荫庇。一毕业,母亲就离开华西坝,赶赴南京就职。次年八月,林则返回中国时路过南京,还专程到中大牙科,苦口婆心动员母亲回华大。那时候母亲正深为亲自能在中国自己的大学里,独立培养中国的牙医人才而自豪, 便婉谢了林则的邀请。
这是母亲第一次违背了恩师和教会对她的厚望。
但是,历史对她开了个玩笑。
1937 年“七七事变”,10 月抗战日紧,南京中央大学内迁四川。包括中大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在内,同华西、齐鲁、金陵等五大学在华西坝联合办学,于是,母亲以国立中央大学教员的身份回到了熟悉的华西坝, 并于 1938 年转回四校合一的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林则、刘延龄、吉士道(三人均时任牙医学院教授)对此非常高兴。
四校合一后 1938 年的教职工名册(存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
这时,林则再次许诺送母亲到加拿大留学,已经写好了推荐信;以后又表示要把女生院交给她来管理、当系主任等等;殷切希望她终生侍奉上帝。
华西协合大学毕业后,1939-1946 年间的黄端方
爱情的力量,让黄端方第二次未随恩师之意。那时候,她认识了也是因抗战而内迁到成都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主任陈之长,1939 年,他们结婚了。婚后,母亲离开华西坝住到了西边不远、位于南门外的血清厂,继续在华大口腔病理学系任教。像读书时一样,除了教学,她的科研工作也很优秀。
2020 年 11 月份,我再次从川大档案馆查到一份 1945 年的案券,是当时华大口腔病理学院院长戴述古〔1934 年华大牙学院毕业。著名的口腔医学家,开创了我国口腔预防医学事业(参见《华西口腔百年史话》王翰章主编)〕为黄端方发明牙组织活体染色研究成果,而呈报教育部的授奖申请函(见照片),函文中称:……本校口腔病理学系副教授黄端方发明牙组织活体之研究,于牙医科学上,系属创举,其贡献颇大。特请恳奖励……云云。
1945 年华大口腔病理学院院长戴述古为黄端方申请科研奖呈教育部函(存四川大学档案馆)
照片为科研中的黄端方和刘延龄(照片由何溢牧师提供;原件存耶鲁大学图书馆。
科研中的黄端方
这段时期,母亲与在华西的很多同学、同事和学生都成了终生的好友。比如雅安人乐以成(1904 年生,妇产科学),资中同乡蒋高第(1906 年生,内科学)和刘昌璠(1910 年生,1936 年毕业于药学)以及肖卓然(1908 年生,1932 年毕业,牙科学)、魏治统(1912 年生,1938 年毕业,牙科学)等等。记得 1979 年 1 月母亲去世时,在三医院举行的追悼会上,他们都来了;还记得蒋嬢嬢拉着我的手,动情反复地说:“黄姐去得太早,真可惜了 ”。
这次川大查档,还发现了有关于黄端方和蒋高弟获奖学金的记载:华大 1929 年的预科获奖学生,第一名为蒋高第,第二名为黄端方(另有邱常爵)。有意思的是,此案卷还解决了关于蒋高弟的一个“悬案”:母亲曾经讲“蒋高弟是资中同乡又是同学”,而在成都二医院报告蒋去世的文章里(蒋是二医院内科主任),称她是山东齐鲁大学毕业,38年毕业后回到华西协合大学工作。问题出在哪里,是母亲记错了吗?就是在这个奖学金名单后边有附注写道,因蒋高弟“已提出转学获准退还所交纳学费;但春季的奖金则改由第二名两人平分……”。这说明两者都没错:母亲与蒋在华大只在预科同学了一年, 之后蒋就到了齐鲁大学;到 1938 年后,两人再次成为华大的同事。
黄端方与资中同乡蒋高第同获华西预科奖学金的文案。本文案也澄清了蒋高第就读华大还是齐鲁的疑问(存四川大学档案馆)
合校后的牙科教学部分设在华西坝东端南台路。母亲常会去离此不远的十四南街刘昌璠的公馆过周末。她给我摆过:……那个四合院不大,很精致,总会有好多的客人。有一次我临时有事要进城,主人热情挽留;昌璠的弟弟刘昌永(华大的精神病学创始 人)还拦着说笑:黄姐你别走,我给你翻个跟斗……。母亲到晚年不仅患肺心病,还常受到严重的三叉神经痛的折磨,我记得曾多次去二医院药房,请刘昌永(她任二医院药房主任)帮忙找药。
前年夏天,从上海回四川的 83 岁的表哥吴万先回忆了他看到的一件趣事:假日里, 朋友们来黄瓦街家里聚会。饭后,母亲拿出一堆牙刷,发给每人一把,亲自教大家正确的刷牙姿势;表哥也是那时候知道了刷牙要上下刷而不应该横着去刷。
她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努力向社会普及口腔卫生知识。记得在我小学一、二年级时,母亲就曾带着我,去三医院背后鹦哥巷里的护士学校讲课。让我在讲台上给学员们示范正确的刷牙手法。
第四部分 走出象牙塔,以行医服务大众
1946 年,母亲突然离开了生活学习工作了约二十年的华西坝。这是什么原因?
在她给姐姐陈恕庸的第二封信(1965.12.26)中是这样讲的:“…… 1946 年?,我当时是华大毕业女生中(年龄)最大、班次最高的,薪水是 300 元,同事中比我的班次高的肖卓然(现在上海)也是 300 元;另外有一个犹太人叫乳仁的,他的薪水 290 元。
但一次他向我谈到,学院额外给他 20 元伙食补贴。我就去问林则:院长,凭什么他要拿补贴?院长回答说,他是外国人吃不了中国饭。“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什么国际关系什么间谍关系(黄端方在文革中被批斗的罪名之一就是间谍),只想到我这个中国人受气了。就把什么都丢弃不顾了(我当时正在做白鼠对氟中毒的研究以及镁的缺乏对鼠牙和牙周影响的研究等),就离职了。说什么,我也不再转去 。” 因 10 元的差别引发不平等对待的愤慨,继而离去,这件事很能反映母亲的秉性。
在43岁的中年重新创业,离别学习工作生活了多年的华西坝,离别熟悉的师长和学友,抛弃了所有的名誉地位,优厚的待遇及出国深造的机会。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刻, 或许母亲并未细想今后的路怎么走?……但她 40 年来奋斗的经历,让她相信前途同样可以再造光明;她感恩于华大,诸多良师益友难以离舍,但同十年前一样,她更向往对理想和公正的追求。
离开华大后,母亲加盟由同班同学肖书明、彭志兰在成都提督东街办的协和医院, 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同时也在黄瓦街 41 号家中私人开业。姐姐和表哥都还记得,黄瓦街41 号大门右边挂着一块黑底烫金的招牌:牙医博士黄端方诊所。这个牙科诊所在成都还颇有些影响。我妻子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川大经济系知名学者钟祿俊教授曾对她讲:“你妈妈她五十年前给我补的几个牙,到现在还用得非常好……”。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倒是母亲曾多次对我讲过,自己在口腔诊治中 “走麦城”的事情。她说,要能镶好一口假牙真不容易,自己就遇到过一个老年病人,镶了全口牙,后来调来调去,病人始终不舒服。最后只好告诉这个病人,我实在做不好你的牙了,退你钱吧……。由此可见,母亲不仅有一流的技术,诊治中,对病人更是非常负责任,工作追求完美。
到成都解放,母亲的私人诊所关闭,全部牙科器具都赠送给川西医院。现在,我家里还有母亲留下的镊子、口镜、探针等十余件小器械。
黄端方和女儿陈恕庸、儿子陈泽先(摄于 1948 年)
1948 年,由中国的第一个牙医学博士、华大 1921年毕业的乐山人黄天启先生在四川省立医院(解放后改为川西医院)筹建口腔科,黄天启为主任,邀请母亲加盟,任副主任。到 1953 年新建四川省人民医院,黄天启带着两个业务骨干去了那边;川西医院则改为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黄端方接任口腔科主任。
1950 年前后在川西医院牙科任职期间的黄端方
1963 年在三医院的工作证
新成立的三医院口腔科规模很小,母亲带着没有正规学过牙科的四个人───其中肖道武是在镶牙馆当学徒出身,后来参加西南军区医疗队当护士,到重庆西南医院进修过牙科;曾维吾和蒋玉荷、黄慧贤都是黄天启在川西医院时的助理护士和技工。
此照片为 1972 年拍摄,包括了三医院牙科初创时的五人:黄端方、蒋玉荷、黄慧贤(前排左 2、3、4),曾维吾、肖道武(后排左 1、3);以及1955 年以后陆续分配来的科班生艾应滨、汪苏珍(中排左 1、2)和李敬阳(后排左 2)。
2021 年 8 月,我终于同肖道武取得了联系。已经 94 岁高龄的老人坐在轮椅上,激动不已地给我讲了他们当年跟着母亲的奋战历史:“……那时候病人很多,每天常常有一百人,你妈妈是手把手一点一滴教我们诊断,治疗,手术这些技术”,“我们那时候真大胆,也是逼上梁山,特别是你妈,她是主任要负全责。病人来了,我们几个做检查诊断,她在后头把关,做决定”。“……黄主任对我们要求很严,治疗不准打一点折扣。结果大家都练出了一身本事……,在她的带领下,后来我们也能够做根管,做修复了。” 肖老深情地回忆道:“你妈妈特别善良有爱心,不光教我们技术,严格要求;那时候我的经济条件差,她还常在生活上给我接济”(根据录音整理)。
那个时期,母亲她们是个同甘共苦和谐团结的集体。工作上不计条件不分彼此;生活上大家也相互关心,还记得我与母亲刚搬到三医院住的时候,医院暂时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我们就借住在医院隔壁的 52 号大院蒋玉荷家里,蒋嬢嬢让她的大女儿、与我同岁的谢绍辉去和两个妹妹挤着住,把房子挪给我们用。
从 1955 年开始,先后有四川医学院(即原华大)的口腔毕业生李敬阳、艾应滨、汪苏珍等人分配来三医院,口腔科逐渐规范、形成规模。曾维吾也练成了口外特别是拔牙高手;肖道武和黄惠贤撑起了修复科,肖医生更是成都市知名的镶牙医生,慕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
母亲对她经手的每个病人,都要作细致全面的口腔和牙齿检查,解除病痛之外,还会不嫌脏累地清除牙垢。五十年代农民很穷,总是要熬到牙痛得很难受时才来求医。这些衣裳破烂、经常是汗臭混合着口臭的病人有时难免会遭到些白眼的。这时候我母亲的爱心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诊治牙病之前,她曾用不须花钱的“耳针”给他(她)止痛, 病灶处理完了,还要一边细致洁牙,同时不忘一通严厉的保护牙齿的说教。她还努力学习中医,常给病人特别是农民开中药处方,说“这样可以给他们省点钱”。
华西口腔医学良好的教育,让母亲建立了系统、科学的牙医学理念。
她强调:口腔是消化系统的门户,而牙齿是第一道关,对健康有举足轻重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健康的牙齿始于清洁,基础在于洁牙并建立良好的习惯。另外,她还经常说,千万别小看牙病,不要认为“牙痛不是病”,反正死不了人。她主张一旦牙齿有不舒服,一定要去看专业的牙科医生。还要注意,要保持牙齿的终生健康,早期的良好发育是重要基础。因此一有机会,她就总会对朋友们讲:要让孩子在幼儿期就经常咬硬度如胡豆样的东西,让他的牙槽骨得到充分的发育,为牙齿的健康生长做好准备。她以自己为例,给我讲过:在华大念书期间,林则曾给她做了全口牙的咬合调整,因此她终生不仅有一口令人羡慕的漂亮牙齿,而且胃口好,也因此有健康的饮食和睡眠……。另外,她还不厌其烦地给大家宣讲:真牙齿总比假的好;自己的牙,活的总比死的好。所以,她反对轻易地拔牙,认为这是对患者的极不负责任。在她一生的从医经历中,总是在费尽心机、费时费力地做着抢救牙齿的平凡工作。那时候,一般人对牙周病还不像今天这样重视,但母亲特别强调,牙周病是牙齿松动乃至脱落等口腔疾病的根源。记得她晚年曾深有所感地说:病人牙痛,表现在牙齿上,其实多半根源在牙周。我也因此体会到为什么在科里,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做那些最不起眼的口腔卫生工作。
在口腔科里母亲资历最高,作为主任,总是极尽全力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所有的下属,只要是努力工作、勤恳学习的,无论学历高低,都是积极鼓励表扬;反之,但凡工作不认真、疏于业务者,则会严格批评。
在三医院口腔科的工作照,摄于 1964 年
母亲离开华西坝,在口腔临床医学的第一线工作 26 年,完全脱离了科研教学工作。找到的档案资料里只有两份同她的学术活动有关系,一是 1948 年成都首届医师节的照片;另一个是 1963 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口腔医学年会合影。
图中第三排左起第 8 为黄端方,照片由校友易先德提供。
全国口腔科学大会 1963 年 10 月在成都举行,全国口腔医学专家三百余人参加。部分代表合影。第一排左起:吴廷椿、向壁光、章尔仓、王巧璋、张光簿、张涤生、黄端方、席应忠 (载王翰章编《华西口腔百年史话》,邓长春提供)
现在回想,从她当年的学生毕业论文(A study of Dental Caries and Dietary Conditions among Students in Chengdu),以及 1945 年戴述古为黄端方申报科研奖项的呈文所反映的项目,再到她信中自述,在 1948 年“离职时正在做的科研题目(白鼠对氟中毒的研究以及镁的缺乏对鼠牙和牙周影响的研究),都反映出母亲对于社会民生疾苦的一贯关注。
母亲疾恶如仇、眼里掺不得一点沙子,工作方法简单直接,有时会让同事下不来台难以接受。在我记忆里,母亲非常有爱心但是也很严厉。
不过,年前去看望已经年逾 80 的艾应滨医生,她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记忆里,黄婆婆对大家都很慈祥亲切,不是那种严厉的领导。
到了文革中她被发配去扫马路的时候,在大街上时常会有不认识的人突然近前给她塞上几个糖果,悄悄地问候一句:“黄主任你还好嘛?” 叫她心里暖上好久。好在这些坎坷不久就如浮云般飘散,文革后她也恢复了工作。尽管她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健康状况就很快离职退休,但她对那些文革期间整过她的人和被整的这些事却并不耿耿于怀,见到面仍旧同过去一样的问长问短、打听科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因为口腔科的事情就是她这一辈子最在意的事情。
从象牙塔走到医院治病一线,由病人到病友而朋友,母亲有了许多新朋友。
在黄瓦街家对面少城小学(解放后改为黄瓦街小学)的刘多淑老师,就是从病人成为好朋友的。后来刘老师调到位于青龙街的成都市第二中心小学做教导主任,学校在青龙街成都市三医院斜对门,她和母亲依然是邻居,常来嘘寒问暖。
刘主任的儿子王立是我的中学同学,从他口中,这次听到两件关于黄端方的轶事。这是他母亲讲的:一个是母亲在华西协合大学的时候,有个漂亮的英文名字叫“Rose Mary”;另一个更有趣:在熟识的朋友中,母亲有个外号:“黄牛”,因为她给病人拔牙的时候特别有劲,别人拔不出的牙,她会一下子就拔出来了,其实这是牙科医生一种重要的技巧……。
1971 年在母亲临退休前,她已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及老年支气管炎,还不时发作三叉神经痛,但仍响应医院 “领导带头到第一线”的号召,到成都市东郊洪河院山公社参加巡回医疗三个月。我曾去那里给她送衣服,当时洪河东山一带还到处是山坡梯地,她却像年轻时一样,爬坡上坎去给农民诊治牙病,乐此不疲。
成都东郊院山公社赠送的笔记本

母亲于 1972 年退休。在退休证上看到,从 1948 年算起,她在三医院服务共 24 年;解放后的连续工龄 22 年。
黄端方退休证
退休后,母亲与父亲住在三医院隔壁 59 号大院的宿舍。我当时知青返城,已在四川大学工作,姐姐陈恕庸已经从昆明远郊的电机厂调回城里工学院。父母亲也多次到昆明姐姐家里住上一阵。这段时间,是母亲一辈子最安稳最闲适、享受天伦之乐的几年, 她的慈母之爱也有了最充分的表现机会。
在院子甚至街上,遇到熟人带着孩子,她会弯下腰埋头仔细看小孩的脸和嘴,然后反复告诫说:牙齿很重要,千万别以为反正要换就可以随便对待,别光吃软的,要多咬干胡豆之类的硬东西让牙槽骨有充分的发育;对自己的儿孙辈们,更是视为珍宝。记得我女儿满月,母亲抱起来就舍不得放下,一直到手软才喊龚宓接下。
1972 年退休后在三医院家中
云南昆明工学院校园。图中后立者为姐姐陈恕庸,小孩是姐姐的儿子朗文锦。
前不久,我妻子又向我回忆了母亲给她讲的几桩旧事,令我唏嘘感动不已:
一个是我在眉山当知青,也就是在她退休前后,我骑自行车从生产队回成都,整整一天近两百里路程。到家简直累坏了,躺上床就再不想动。这时母亲心疼极了,在床边给我搓揉放松还一边问长问短。我一句话不说还嫌她啰嗦……;另一件事应该是 1977 年左右,那时母亲的身体已经比较虚弱,但执意要为我织一件毛衣。过了好久,母亲把快要织完的毛衣拿给龚宓看,喃喃地说:“才发现这里打错了一路,……没力气改了,将就了,也算是个特殊纪念吧……”。
妻子讲得动情,我也听得热泪盈盈。
就在今年国庆期间,听说我在写关于母亲的回忆,妻子的姐姐姐夫龚苏和钟兴德向我讲述了他们四十年前对我母亲的印象:他们儿子出生时体质差,5 个月时又到三医院儿科住院,那天黄婆婆拄着拐杖走到病房看望他们。安慰说:“ 从母亲带来的免疫力只保持到四、五个月,生病难免。现在到了医院,有医生的治疗,放心。等他自己的免疫力渐渐强了,就会大不一样的”。末了,老钟特别说道:印象最深的是黄婆婆表现出的那种知识女性的浓浓慈爱之情。
在这里,想再谈一点我童年的居所黄瓦街 41 号院子和生活中的母亲以及我父亲。我的父亲陈之长,1898 年出生于四川简阳县。十五岁时,在成都石室中学以全省第七名的成绩考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他本应该在 1920 年毕业后赴美,但因参加五四运动而滞后一年,于 1921 年到爱荷华州立大学学习兽医学。以后他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兽医学博士学位,于 1926 年回国,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任系主任。1937 年抗战开始,南京紧张后,他上下奔走找到卢作孚的长江轮船公司帮忙,用江轮运载几十头进口的良种荷兰奶牛和教学设备,率员工入川到重庆。畜牧兽医系再辗转到成都,落脚位于浆洗街的家畜保育所(一般称“血清厂”,现在农业厅内),继续教学。经在南京认识的教会朋友杨牧师介绍,认识了母亲黄端方。父亲 1948 年返回四川加盟川大农学院,1956 年农学院在雅安独立建院,他也到了雅安,直至退休。五十年代之初,父亲长住川大,周末才回家;后来又长住雅安,只有寒暑假或者他到成都开会才能见面。直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我才有机会在父亲身边相处。这时 候,我分明感到一位宽厚长者一生所凝聚的力量,转变成细微绵软宁静温馨的爱意向你弥散,让你镇定开阔。父亲在他 89 岁时患结肠癌于 1987 年 3 月去世。
前已提到,母亲 1939 年婚后就同父亲住在浆洗街农业部血清厂院内(现在的省农业厅位置)中大畜牧兽医系宿舍,到 1946 年离开华大后,这时陈之长已经随中大光复迁回南京。于是母亲带着 6 岁的姐姐回黄瓦街 41 号老宅住,我次年也在这里出生。
黄瓦街位于成都少城,与长发街和娘娘庙街(五十年代末被拆除,剩下一半改名商业后街)毗邻。41 号院子不大,但与别的院落不同:院坝北面,临街是一排住房,其他地方,占去一多半的是一片瓜菜和果树。菜地东南角,有个带粪坑的旱厕,周末父亲进城回家,就会挽起袖子,从粪坑里舀粪挑到地里施肥。每到这时,我和姐姐就会兴高采烈的跳上跳下帮忙。姐姐还记得,她曾在地里摘了好多大白胡豆,也曾从自己窗下拔起一棵结了好多果实的花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菜地中间那七、八棵苹果树:每年冬天, 父亲会在苹果树周围挖上一个圆形的沟,灌上粪水──难怪结的麻皮苹果又脆又甜。母亲很喜欢这个地方,总会端个凳子坐在地坝边,笑眯眯的看我们忙活;还把苹果带给科里的同事们品尝。
五十年代初,口腔科同事蒋玉荷的表妹石永萱大学毕业没有工作,到我家当保姆, 我们都叫她石大孃。父亲住在东门外的四川大学,母亲日夜在医院奔忙,家里的里里外外大小事情全部由石大孃一手操办,让母亲能够安心去操劳医院和科里的工作。
黄瓦街距离母亲上班的川西医院不远,大概不过十分钟距离。我记得,她每天除了上下班走两次(中午就在食堂吃饭),晚饭后还要去医院学习,多数时候等不到她回来我已经睡着了。
那时候母亲 50 出头,年富力强。和她干脆明快随和的性格一样,她最喜欢白色。家里的物件,除了一片毫无装饰的白色墙面,所有的毛巾、脸盆、茶杯全是白色;母亲的服装也是素色,夏天是白色衬衫、到了秋冬装也多是浅色的米灰色;好像就从没见她有过花的着装。房间里,除了睡觉的床、装衣物的大箱子,只有写字台和椅子,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
母亲喜欢食辣。最喜欢的菜是干煸苦瓜和素炒红油菜台,但都会沾着醋吃。还记得石大孃那一阵中午往三医院送的饭盒上边除了油菜苔,总是有一碟红红的辣椒油。
1956 年,父亲母亲、姐姐和我。摄于成都
母亲从 60 岁以后就患有的冠心病和老年性支气管炎,在退休前后病情更为加重,逐渐发展为严重的肺心病。
1978 年冬,因感冒引起继发性肺炎,母亲住院 13 天后,于 1979 年元月 13 日在成都市三医院去世,她刚刚过了 76 岁生日。
1981 年夏,在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之后,我骑着自行车,把母亲的骨灰盒送到资中龙江镇百合六组,安葬在母亲的姐姐黄贞和姐夫蔡耀文的墓旁边。
母亲这一生走过的路,正是她名字的写照:端方正直、淡泊明志。
去年清明,到资中龙江扫墓,静静的慈竹林里,一字排开三座墓。最右侧是母亲 的,两尺余高的墓碑上只有简单的三排字:《1903-1979 牙医师黄端方之墓》。这是按父亲的意愿镌刻的。
竹叶沙沙,默默面对已经斑驳风化的墓碑,母亲的身影一一浮现。她的经历,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却饱含了我们民族的各种优秀品质。
“行医兼作个人佈道者”,她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没有教会委派,却是一个无宗教色彩的“布道者”,虔诚地行医布道。
后记
本文发端于 2019 年 5、6月春夏之交。当时,通过老友陈拯介绍,结识了远在美国西雅图的华西校友裴冀。裴老师希望我能够写一点关于黄端方的回忆文章,热情鼓励并晓之以理。促使我开始查证线索、整理资料并动笔。
2019年7 月,在川大档案馆学生学籍部档案里,查到黄端方 1928 年入学后完整的学籍档案资料,据此开始动笔;次年 9 月,在我姐姐处发现了母亲 1965 年为女儿填写入党申请书所需而写的两封信,提供了详尽的个人资料,我忆文的内容由此得以充实。虽是母亲的亲笔信,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多方求证。经过川大档案馆的向红老师介绍,于2020年12 月,到了中国第二档案馆(位于南京市),查找有关中央大学及抗战内迁成都华西坝的材料。──真是不虚此行!通过二档馆利用科刘长秀老师的热情帮助和指导,我查到了 1938 年联合建校时的教员花名册。这一下信心和兴趣大增,陆续又两次从川大档案馆找到能反映母亲入校初期以及四十年代任教时候的表现的重要材料。接下来,2021年初,通过成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何溢牧师,认识了热心华大历史的邓长春老师,多年来,他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从他那里,文章内容又丰富不少,而且有重要的修正。其间,又辗转联系上在美国的易先德老师并从他那里得到有用的线索,还见到刘昌璠的孙子严华,验证了一些提法。近来,还见到了仍健在的肖道武医师……。总之,文章一旦展开,就一发不可收拾。历经两年多时间,文章才得以成型。
对于这个版本,仍然有诸多不满意之处。至少有两点遗憾:第一,是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人事部,没有黄端方的档案!如果能够查到,一定会有很多母亲后三十年的记载;第二,关于黄端方第二次离开华西大学的始末及准确时间,目前只能以母亲本人1965 年给女儿的信件和 1945 年的戴述古报奖呈文为依据,如果能够在黄端方的私人档案之外进入四川大学档案馆进一步查阅,或许能够找到更多的佐证?
两年来,通过对忆文一次次的补充和修改,我似乎跟着母亲,从资中沱江边的贫民家里,走到荣昌、内江和成都,从华美女中走进华西坝,到达象牙塔尖;再回到平民中间,在临床第一线为病员服务直到终老。
广阔深厚的博爱精神,是贯穿她一生的基线。
孟子云:“ 仁者爱人”、以爱而生智慧,以爱而得快乐,以爱而臻秀美。这里似乎还可以添上一句:以爱而添勇气。爱是一种顿悟,是人生一宗宝贵财富。爱可以是浓烈奔放的,也可以是平静含蓄的,但必须是不掺杂一点水分和经久如一的,它必须是由衷而发自内心的。
我没见过母亲进教堂、作祈祷,我想,她也记不得诸多的教义。但我相信,在母亲的心中,一定住着一个上帝。她那些悲天悯人的情怀,无私的付出,艰苦地求学,默默地忍辱负重……都是源自从小到大受到一个个有名和无名的中外朋友们,通过文化、科技,医学和宗教,所给予她的那些协和坚韧崇实精神。她永远记住了、并且一生都在实行——用给予自己恩惠那些人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世人,就是对上帝的最好回报。
在漫长的忆文写作过程里,得到陈拯、王立、艾应彬、肖道武,我夫人龚宓、姐姐陈恕庸、表亲吴万先、夏继明、夏继文,以及龚苏、钟兴德、黄卫东、黄英、蔡益等众多亲友的关怀和帮助。
其间,我在北京和合肥的大学同学吕小庆、孙兆琪为我的档案查找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在资中,60 多岁的表亲刘昌学驾驶摩托带我在城里城外,上下找寻母亲当年的出生地。
本文所选用的全部图片包括部分档案文字资料,都经过老朋友老同学王立细致的清理,才达到了现在的效果。
在资料收集整理中,给我极大支持帮助的,还有华大子弟邓长春、易先德以及严华先生;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的刘长秀老师,四川大学档案馆的向红老师;成都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何溢牧师。
尤其想要指出:如果没有华西校友会裴冀会长自始至终的帮助关怀,该文是不可能面世的。从文章的立题、材料的收集组织到整理成文,她都反复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现在,终于可以用这个集体的劳动成果,向所有关心支持整理黄端方历史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谢意了。
谨以此文献给亲爱的母亲和她的母校华西!
陈泽先
2019年9月初稿
2020年后多次补充修改
2021年10月完稿于成都青城山
作者简介:
陈泽先,黄端方之子,1947年出生,成都13中高66级学生。1969年下乡插队到眉山县当知青,1972年大招工到四川大学宣传部当电工。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在光学教研室工作。曾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次科研奖项。在工作期间报考了本校在职研究生,1986年获得四川大学颁发的首位职硕证书。2007年从 四川大学基础实验中心退休。
编者注:
①1936年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毕业生中共有三位女性:黄端方、张琼仙,同为中国第一批牙医学女博士;另一位为华西口腔历史上最早的女留学生(俄国)谢尔琪(Eugenia A Sharevitch),在华西各种历史文献及研究的文章中,尚未查到谢尔琪踪迹。近期校友之子陈一宽经追索,了解到她后来移居美国旧金山,就职于加州大学医学中心。
②黄端方入学注册名即本名,在校时常被写作黄端芳,直到退休亦被写为芳,因读音相同,也不以为意了。
③张书林,后用同音名张舒麟,毕业后留校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牙科全时间临床医师,两年后(1938年)应新建的国立贵阳医学院之请到贵阳,创立该院口腔科(今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前身)。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