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圣俞诗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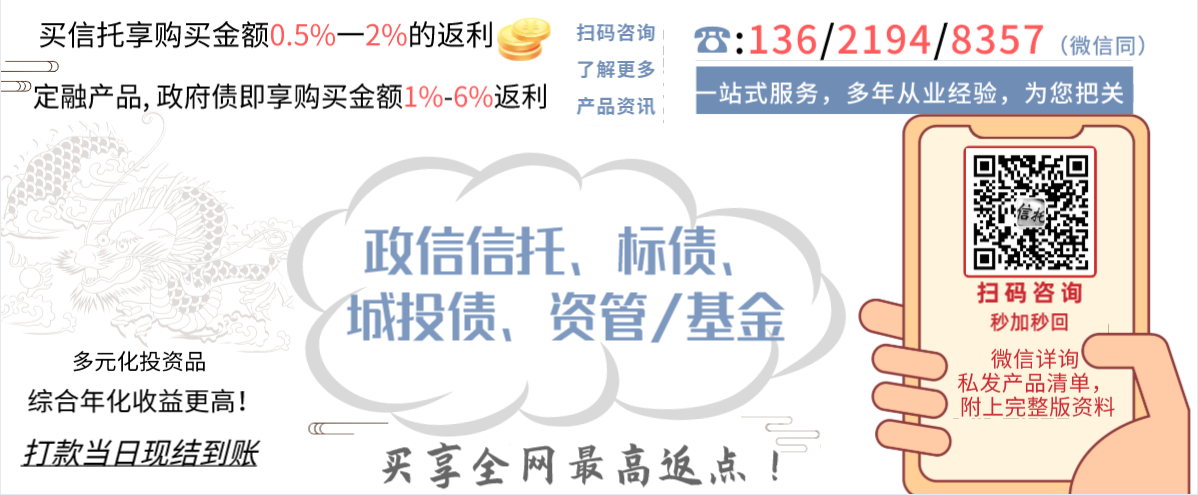
作者:【宋】欧阳修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1],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馀年[2]。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3],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4]!”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注释:
[1]荫补为吏:梅尧臣少时应进士试不第,不能授官,以其叔父翰林侍读学士梅询荫,任河南县(宋西京河南府首县)主簿,乃职品甚低之佐吏。朱熹《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县之属有主簿,秩从九品,县一人,掌县之簿书。凡户租之版,出内(纳)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违与其财用之亡失,以赞令治,盖主簿之为职如此。” [2]困于州县凡十馀年:梅尧臣后又调任河阳县主簿,建德、襄城县令,监湖州盐酒税,佥书忠武军(许州)、镇安军(陈州)节度判官等,皆州县佐职。 [3]宛陵:宣城旧称。 [4]王文康公:王曙,字晦叔,宋仁宗时官至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卒谥文康。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载:“王文康公晦叔,性严毅,见僚属未尝解颜。知河南(府治在今洛阳)日,梅圣俞时为县主簿。一日,袖所为诗文呈公。公览毕,次日,对坐客谓圣俞曰:‘子之诗,有晋宋遗风,自杜子美没后,二百馀年不见此作。’由是礼貌有加,不以寻常待圣俞矣。”
赏析:
宋初诗文革新运动中,梅圣俞是欧阳修志同道合的挚友。欧阳修对梅诗非常赞赏和喜爱,屡加褒评。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他为梅诗初次结集而写下这篇序言的主体部分。仁宗嘉祐五年(1060),汴京大疫,圣俞于四月间病逝。次年,欧阳修亲自为梅诗整理编撰成书,并续完此序。
文章开头难,也最易见功力。俗话说:文章好开端,成功已一半。确有道理。优秀的古文名篇,发端总是精心结撰,气象万千,振起全文,开合自如。本篇第一段,即是工于发端的一个范例。

这一段的成功,首先在它提炼出“穷而后工”这样一个千古独创的命题,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类似的意思,前人也有所表述。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唐韩愈《荆潭唱和集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等都是,但都不如“穷而后工”这样言简意赅,清楚明白。
欧阳修推出这一命题也极具匠心。他并不急于求成,一泻无遗,而是针对世情,从容曲折。文章先引述一个似是而非的世俗论调“诗人少达而多穷”作诱饵,慢慢引钓,以求大鱼。世俗所见,因为写诗,所以使人穷,唐代大诗人杜甫甚至愤懑地慨叹“文章憎命达”。“夫岂然哉”,用反问句作顿挫,妙在疑似之间,而实际上已隐含否定之意,含蓄有力。接着一句:“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写得扑朔迷离,似乎在为世俗论调作辩解,肯定其是;其实是妙语双关,为展开论述奠定根基。
论述伊始,作者用“凡”字总起,可知是考察和综合了大量诗歌现象的结果,并非一知半解或以偏概全,显示了论述的深广度。“穷”的标志是在政治遭际上的不偶,而非生活境况上的困苦——那叫做“贫”。《孟子·尽心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说得很清楚。当然,政治“穷”与生活“苦”,往往是一胎孪生子。所以,栖身草野或困于州县做小官,都属于不得志的“穷”。穷者为什么能“写人情之难言”,而且愈穷愈工呢?因为他们具备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内心有忧思感愤,喷薄倾吐为快;外见充满生机的自然万象,尽可寄兴托意。因此,在这形象思维的沃土上,穷者能“兴于怨刺”,创作出大量优秀篇章。这样的例证,历史上可以举出许多,屈原是最典型的。他的不朽长诗《离骚》,就写于被放逐以后。所以梅圣俞《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说:“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如果屈原仕途得意,青云直上,岂能有《离骚》?文章在论述了“愈穷则愈工”的道理后,最后用两句作一收束:“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水到渠成,点出世论之误;“殆穷者而后工也”,揭出千古名言。
这一段的成功,还表现在它统摄全文,是后面展开叙述和议论的灵魂,牵一发而能动全身。没有这一段,后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黯然失色。本文的主角梅圣俞在此只字未提,好像不着边际,然而联系下文细加吟味,方知此段议论处处影射圣俞,并非泛笔。点题而不着痕迹,确是文家上乘笔墨。
第二大段紧承上文,正写梅圣俞其人其诗。第一层承“穷”,第二层承“工”,第三层感叹其“穷而工”。
叙写梅圣俞的经历,用笔简练而语带感情,其侧重点在反映其穷。从“少”开始,到“年今五十”,其中不少时间词,概括了梅的仕历,屈身佐吏,沉沦下僚,长达近半个世纪,确是“穷之久”。“辄抑”、“困于”、“犹从”等语,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平与同情。“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这一句上结其穷,下启其诗,并与首段“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相照应,相当巧妙。
梅圣俞诗之“工”,文章从多角度予以反映。首先写他从“童子”开始即有诗才。接着用其文陪衬其诗。“简古纯粹,不求苟说(悦)于世”,补出了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的原因。梅圣俞“学乎六经仁义之说”,满腹经纶,但不愿阿附世风,不以浮艳柔靡的文字去猎取功名。这句赞其文风之正,人品之高,很有分量。而“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又深深叹惜,也包含着对主考官无识的谴责。接着写他诗的内容是“不得志”,扣住“穷”字。其数量,则“于诗尤多”,又为下文三、四两段的编诗张本。最后写世人对其诗的推崇。前面“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是概写,以见广度;再用王文康公语作赞,是特写,以见深度。有点有面,极写梅圣俞诗之“工”。诗虽工,世虽知,竟未得其用,“未有荐”、“不果荐”两句感慨系之,由此引出下一层的议论和抒情。行文细针密线,极具匠心。
第三层就“穷”和“工”在梅圣俞身上的体现兴发感慨,写得有波折。“若使”这一长句是虚写,作者希望两全其美,即梅圣俞既能在朝廷做官,又能写歌功颂德的“雅颂”诗。但是在道理上有矛盾,即诗人倘不穷,又安能工诗?清代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按语就说:“果其进于朝,工于铺陈功德,恐无传世行远之作矣。”其实这个道理,欧阳修何尝不知!他在《薛简叔公文集序》中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欧阳修的内心,只是殷切期望老友能脱穷得达,其目的如文章开头所说,是士“蕴其所有”,当“得施于世”,以实现其“致君泽民”的抱负,若不凭借一定的权位,就难以展其长才。为了摆脱“穷”,宁愿牺牲这个“工”,所以只要“得用于朝廷”,然后去写些歌颂大宋功德的诗也是“岂不伟欤”的。但看来也未有“得用”的可能,所以这只是虚设一愿,从反面加强对其“不达”的愤叹之意。“奈何”句陡一转折,是实写,回到无情的现实,梅圣俞终究只能写“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穷者之诗!这感情上一扬一抑的对照,把无奈和惋惜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一句“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用“工”、“穷”、“惜”三字总束第二大段,又密切照应了首段,文情妙绝。
三、四两段写对梅圣俞诗编次的情况,谢景初编之于生前,欧阳修编之于殁后。两段不仅反映了梅圣俞诗作之多,更表达了欧阳修对他的倾慕和哀痛心情。“嗜”、“遽喜”、“辄序而藏之”、“哭而铭之”、“索”、“掇”等动态词的运用,准确生动,而且一往情深。前人曾论“此篇是欧公最作意文字”,就其全篇感情之深、结撰之精、下语之警而言,实为笃论。
欧阳修文章与韩愈深有渊源,这篇可作显证。韩愈写过一篇《送孟东野序》,也是就诗兴感。写作的对象孟郊是“善鸣”而不得志的人,韩愈希望他得志,以“鸣国家之盛”,不希望老天“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欧阳修在本篇中表达的对梅圣俞的感情和希望,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韩文称“不平则鸣”,欧文谓“穷而后工”,两语同富有创造性,堪称工力悉敌。








评论列表